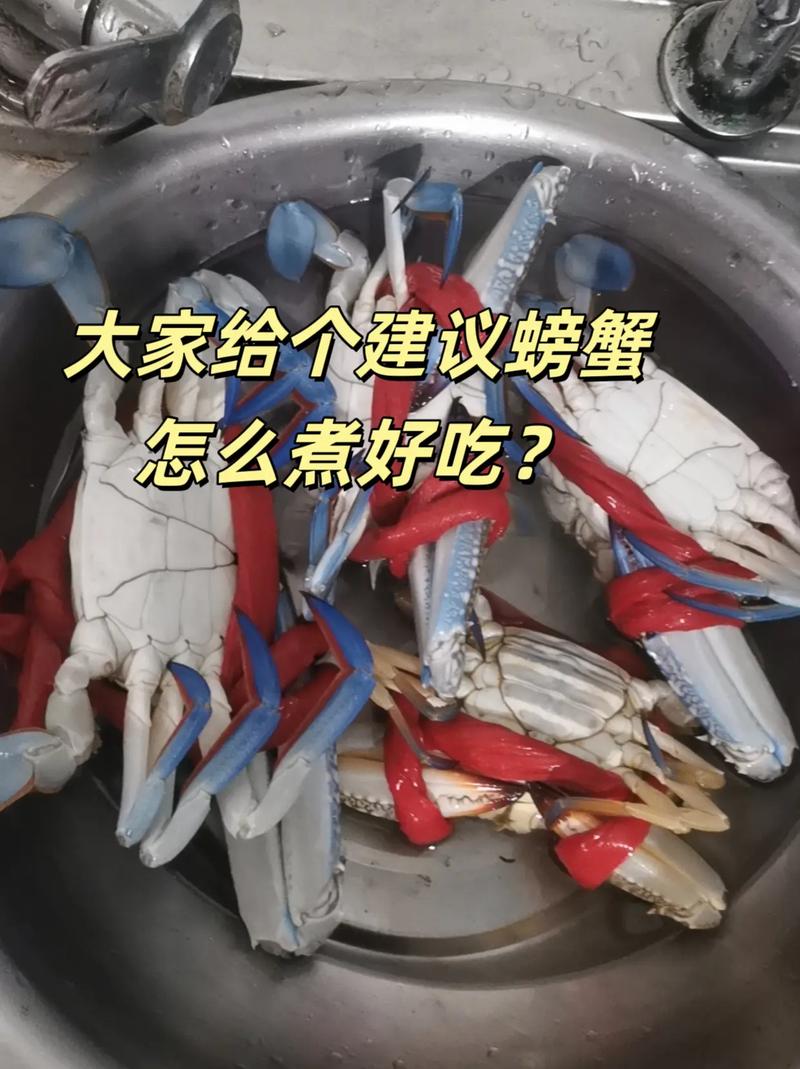家族A的史册,写在面粉的肌理里。它们来自一片被反复碾压、休耕、再碾压的苏北平原。雨水是吝啬的记账员,日照是严厉的监工。麦粒在此地学会的生存哲学,是向内收紧,将淀粉质构筑得紧密、倔强,像一层层压实的年轮。这决定了它们的后代——面团——天生带有一种“拒水”的尊严。寻常的温水无法令其动容,需得是滚烫的、近乎暴烈的沸水冲入,才能短暂地瓦解那层心防,激出些许黏性,当地人称之为“烫面”。这并非柔和的和解,更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淬炼,留下内里半生不熟的骨气。家族的信条是:柔软即是溃败。
家族B的纪传,则浸渍在油脂与时间中。并非精炼的、清透的油脂,而是猪板油在文火下缓慢析出的、带着微黄与细小油渣的荤油。它冷却后凝成乳白的膏体,有动物性的醇厚气息。这个家族的历史使命是渗透与离间。它们携带花椒与粗盐研磨成的细末,准备在面团层叠的迷宫中游走,目的是让家族A那紧密的联盟产生美妙的、酥松的裂隙。它们的胜利不靠团结,恰恰靠制造分离。

(图片来源网络,侵删)
联姻的过程,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反向操作。直觉说,将烫好的面揉光、醒透,待其温顺。不。此刻需趁热,趁那面团还在烫伤的惊愕中未曾回神,将其粗暴擀开。直觉说,油酥应均匀涂抹。不。需用冷却成膏的荤油酥,以不规则块状甩上,像一场局部的、油腻的雪。直觉说,卷起后应顺纹理擀圆。不。需将面卷拦腰斩断,截面朝上,狠狠压扁,让那些被切断的油层,成为未来酥裂的伏笔。直觉说,烙饼用中火,耐心候其熟成。不。烧烫的铸铁鏊子,需淋上足量的油,近乎炸的态势,将饼坯掷入。高温瞬间封锁表面,内里未化的猪油块在沸腾中制造暴动,蒸汽尖叫着从裂隙冲出。
后代,便是那出锅的“穿城大饼”。它不再是敦厚朴实的圆脸,而是一张布满不规则焦痕、边缘炸裂如地理图谱的狂野面孔。手感极轻,指尖稍一用力,便簌簌掉下琥珀色的脆皮。咬下的声音,是密集的、细碎的咔嚓声,像踩碎一片冻硬的秋叶林。层与层之间,是油酥离间成功的、干燥的虚空。面香不再是主导,那股炙烤过的动物油脂的焦香,混合着花椒的麻意,成为贯穿的主线。它很烫,热度藏在每一片酥壳里,耐心地灼着舌尖。
剩下的半块饼,我把它搁在窗台,苏北的穿堂风正吹过,饼屑被风卷起,像一阵干燥的、可食用的雪,落在楼下阿婆晒的干辣椒上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