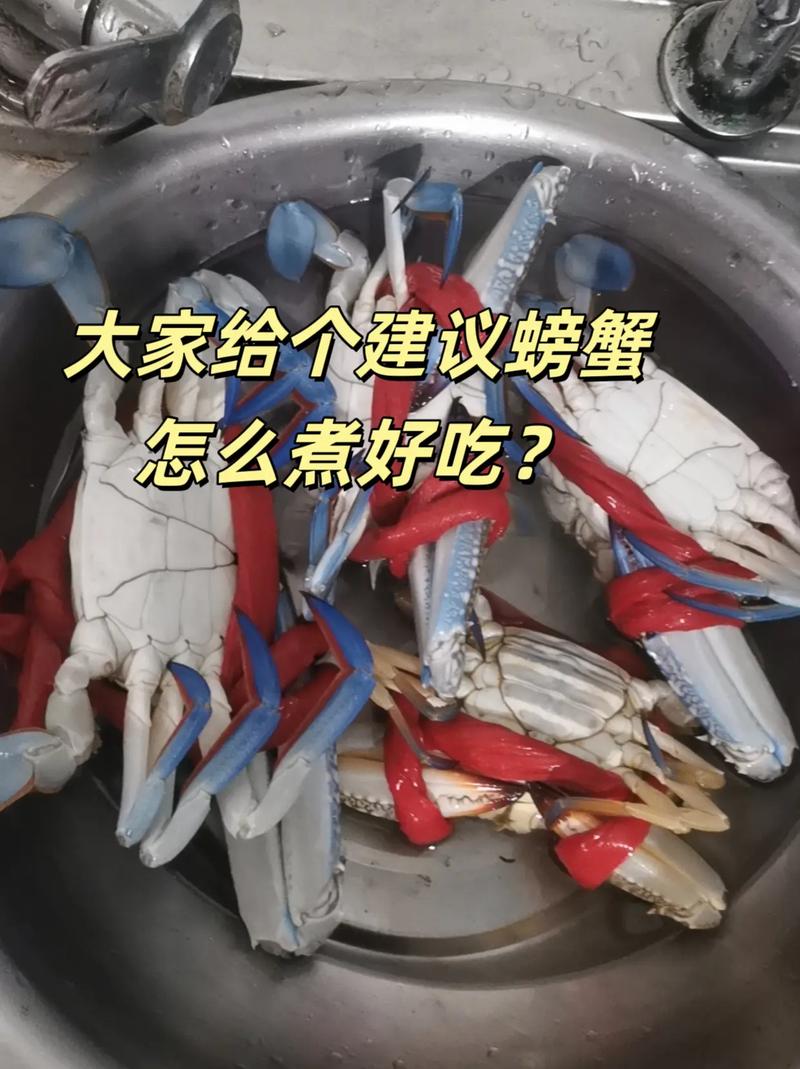昨夜又梦见外祖父。灶膛的火光把他灰白的鬓角映成一种暖金色,他背对着我,肩膀随着某种节奏轻轻晃动。空气里有禽类羽毛遇热的微焦气,混合着陈年黄酒的甜润。他转过身,手里托着一只完整的、油光锃亮的鸭子,可我凑近看时,那鸭腹的开口处,隐约又露出鸽子浑圆的轮廓。醒来时,舌根残留着一种复杂的、层层叠叠的鲜,像一口深井,丢下石子,要过好几秒才听到那一声遥远的、来自最底层的回响。我决定试着打捞。
第一幅:解构的秩序。
传统的套四宝,是鹌鹑套进鸽子,鸽子套进鸡,鸡再套进鸭,一种严丝合缝的、宗法式的拥抱。我不想要那种秩序。我从市场带回的,是一只肥硕的麻鸭、一对乳鸽的胸肉、半只走地鸡的腿肉,以及一捧鹌鹑蛋。它们被平等地摊在榆木案板上,彼此分离,互不隶属。拆骨是个冥想过程,刀刃贴着禽类的骨骼游走,发出细碎的“嗞嗞”声,像在剥开一层层温热的、有生命的铠甲。肉被片成大小不一的薄片,筋膜则另置一碗,待会儿,它们会在汤里化成无声的誓言。
第二幅:汤的独白。
铸铁锅底,先铺一层姜片,再是那些剔下的筋骨。冷水漫过,小火催着。血沫是第一批浮上来的、仓皇的逃兵,撇净后,世界便清明了。剩下的,是时间与温度之间漫长的谈判。汤色从混沌到清亮,再到一种近乎琥珀的淡茶色,需要四个钟头。这期间,它只在表面偶尔破裂一个气泡,像一句轻得不能再轻的叹息。这锅汤,将是所有离散肉片的粘合剂,是梦里的那口“井”。

(图片来源网络,侵删)
第三幅:非嵌套的组装。
我不准备把它们一个塞进另一个的腹腔。取一只宽口的粗陶钵,底部垫上焯过水的冬笋片和香菇,它们像河床稳固的卵石。然后,开始毫无章法地、一层层铺叠:鸭肉片(带着皮的那面朝上,期待油脂被热力逼出的脆响)、鸡腿肉(肌理紧实,颜色稍深)、鸽肉胸(最娇嫩,几乎是粉白色的)。每铺一层,就淋上少许薄盐和那琥珀色的原汤。最后,将煮到刚凝固的鹌鹑蛋,像埋藏宝藏一样,半掩在肉片之间。这不是嵌套,这是地质沉积。
第四幅:蒸汽的判词。
陶钵蒙上耐高温的油纸,再盖上厚重的钵盖。送入蒸箱,剩下的便交给汹涌的、无所不在的蒸汽。一个半小时,是一个足以让坚硬变得柔软、让分离走向融合的时长。蒸汽在狭小空间里循环往复,带走生腥,留下汁液,迫使每一种肉的本质——鸭的醇厚、鸡的鲜甜、鸽的细腻——相互渗透,边界开始模糊。
第五幅:揭盖的瞬间。
油纸被蒸汽顶得高高鼓起,像一面濒临破裂的鼓。揭开时,没有预想中扑鼻的浓香,只有一团滚烫的、湿润的雾扑面而来,带着所有禽类精华被浓缩后的、近乎沉重的气息。雾气散开,钵内景象平静:汤汁清浅,刚刚没过最上层的肉,肉色都已转为沉静的浅褐,鹌鹑蛋则像温润的玉珠嵌在其中。撒上一小撮切的极细的香芹末,绿色落下,瞬间便有了生气。
用汤匙舀下去,必须穿透所有层次。一勺里,有鸭皮的微韧,鸡肉的丝缕,鸽肉的茸感,和一枚完整的、颤巍巍的鹌鹑蛋。送入口中,那种“鲜”不再是线性的、单一的,而是立体的、同时发生的。鸭的油脂香最先漫开,随即是鸡的底味托住它,鸽的清雅在中间调停,最后,鹌鹑蛋的蛋黄在舌尖化开,留下一抹沙沙的、矿物质般的回甘。咸味很淡,仅仅是为了让这场“对话”得以清晰呈现,它确实是舌头与那些熬煮出的氨基酸、与汤中微渺矿物质的古老对谈。
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,信纸上的字迹也有些模糊。钵里的汤还温着,我留了半碗,明天或许会用来煨一小把青菜,或者,就只是兑点开水,在清晨喝下去。外祖父在梦里始终没有回头,但那口井里的回响,我好像,听见了。